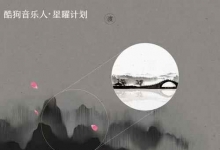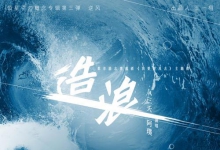“捱过了冰冻三尺怎还怕料峭春寒痛楚与贪”是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出自歌曲《倒春寒》,演唱者是歌手李雨。
这首歌发行于2021-08-10,收录于李雨的专辑“造化”中。
这首歌的完整歌词和专辑介绍如下:
 倒春寒 - 李雨
倒春寒 - 李雨
词:李雨
曲:李雨
编曲 Music Arranger:王于陞Vinson Wang
制作人 Producer:王于陞Vinson Wang/李雨Rain Lee
吉他 Guitar:许华强 Jonathan Koh
和声编写 Backing VocalArranger:李雨Rain Lee
和声 Backing Vocal:李雨 Rain Lee
录音师 Recording Engineer:王于陞 Vinson Wang/许华强 Jonathan Koh
录音室 Recording Studio:Embassy Studio@BJ
混音师 Mixing Engineer:陈宇轩 Jovi Chen
混音室 Mixing Studio:白鲸录音棚 white whale studio
迅雷之势 乍暖
只觉痛快 不知所以然
冰消雪解的边缘
我先放过我 已经很果敢
春寒 倒返
死而复生 生而颤颤
翩翩骤雪 是我撕碎的白衣衫
当我祭奠你 一朝之患
何以区分柔软 腐烂
恨与心不甘
若我长睡不知时节
怎知它朝云暮雨 诡计多端
何以狠狠区别是日新伤 陈年旧疾
痛楚与贪欢
哪知此番是残冬未尽
或是早春倒冷回寒
捱过了冰冻三尺
怎还怕料峭春寒
捱过了冰冻三尺
怎还怕料峭春寒
捱过了冰冻三尺
怎还怕料峭春寒
捱过了冰冻三尺
怎还怕料峭春寒
滴水 石穿
这血肉之躯 一身事端
灰霾遍野 于我是不足挂齿的磨难
当我孕育我 早晚通透绚烂
何以区分柔软 腐烂
恨与心不甘
若我长睡不知时节
怎知它朝云暮雨 诡计多端
何以狠狠区别是日新伤 陈年旧疾
痛楚与贪欢
哪知此番是残冬未尽
或是早春倒冷回寒
是日新伤 陈年旧疾
痛楚与贪欢
哪知此番是残冬未尽
或是早春倒冷回寒
李雨 专辑 造化 中 倒春寒歌词创作表达的意思
一个水底冒出的小气泡,无论历经多深的积攒,不管承受再大的压力,随着离水面越近,虽越是让人难以忽视,在突破临界那一刻,倾然而泄,却幻化为无形,再不被重视。宁可让一切,摊在烈日下“那些难以忍受的人性,那些倾轧而来的压力”让噪音现出原形让造化清晰可见每一段隆起、每一个裂隙每一面烧灼、每一处伤疤都能诚实的被目睹留下那些曾喷薄而出的、曾缓慢流淌的曾逐渐干涸的、曾固化成茧的遗迹是心智的足迹是无私的接纳听见苍穹大地之间看见心智意识之侧打开领略的眼睛感受天地的脉动一个念头都能化作诗一帧画面见证过永远十一个面对自我的独家时刻成就一个通透澄明的个体李雨第四张全创作大碟《造化》从不为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个顺应当下的自然演变,有其内在成因,有其固有逻辑,在每一丝一缕的微小因子牵引下,长成最终模样而盖棺论定,不是单纯因果的拆分,而是一串连结的“化学反应”。从《鱼里言吾》、《浮世游》中企盼以鱼的视角隔着容器旁观万千世界:这侧的水花难以撼动彼岸的涟漪;抑或落入《万千观止》中隔岸伸着长臂用肌肤轻触世态炎凉,而后被情绪与不解反嗜,找出标的逐个报复,既是种宣告,也试图说服自己;如今看透那份通透其实从未离身,只是没找到正确的配方开启它,让自然深根心底,让自在与不解音浪握手言和,彼此长生共存,即便此次不再旁观,活生生的被是非包裹,也不随之愤恨难平,不让杂音的存在消解心底的坦然。《造化》是座遵循世道逻辑的火山,喷薄而出的情绪、丢掉的那些奔腾与不解,全在时间与空间的推移下,覆盖一层新生,她毫不掩饰、棱角分明,但也只有回归常温,才有馀力拥抱天地馈赠,才有底气走向永恒,每一寸看似崭新的肌理,其实来自心底深处的脉动,既不为趋炎附势而生,也从未背弃自我踽行,藏在深处隐隐地跳动着,等着某一刻被意识意会,被自我接受,终而能够再看见天日,每一个用力感知世界的触角,逐渐长出它们原本该有的棱角,然后再偶遇每一次的矛盾中,让创作永不止息。“先打好基底,然后放手,让每个决定长成它该有的样子”在这张专辑中,听得见令观众欣喜也最熟识李雨的样子:《风雨桥》中惯常的动人叙事与民谣基底,一字一句刻画的众生日常;也能听见另类摇滚般的《烈日柬》、异国风情浓郁的《击鼓传花》、丰厚电气味的摇滚歌曲《蝇》;抑或《荒岭十二象》在独立电子的基调上结合摇滚元素,甚至能在其中听见选自歌剧《丑角》中咏叹调《穿上戏袍》的混搭,会有这么大的落差追根究柢地是想让每一首歌曲长成它原本被创作时该有的样子,“李雨在音乐性上始终没有给过自己要求,刻意去强调音乐性很容易陷入一个死角”,“音乐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为了辅助整个创作的”,如同在创作的初衷上,并非刻意为之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张开触角的灵感泉源,从过去碰触到一个确切的故事,慢慢宏观地长成被一个念头打动,拥有更多想像空间的李雨描述:“追求的还是画面上的东西,和之前一样的部分是,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脑补出电影一样的画面和运镜,只是视角以一个旁观者变成被这些景观包围的人”,创作与音乐风格其实从未改变,有的只是顺从了李雨“个性里那部分的尖锐和沉重”,在听感上略有差异。“自然成为消弭内在矛盾的最佳透视镜”—《倒春寒》、《流鸦》、 《荒岭十二象》造化以无为作为自然保护色,其实是容纳万千演变的浩瀚,与之相较,那些复杂难以捉摸的人性、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相互攻讦的恶意好像都那么地渺小、不足一谈,“人虽渺小,但做为一个创作者,能够在宏观的自然与微观的心智中,看见每一寸肌理运作的轨迹,走过那些相对低谷的时候,诚实地摊开它而成就了这些歌曲,达成跟当时的自己与那个状态对话,同时让听见的耳朵受到抚慰或改变那么一点点,倘能如此那这些过程也就非常值得了!”《倒春寒》人们总是热爱标记混沌机制里不被逻辑制约的那一块反常,就像“倒春寒”描述初春时万物甫复苏那段温度快速爬升陡而下降的时节;又如刚进入秋季缓步凉爽却突而燥热的“秋老虎”,系统性的纠错总有段貌似失控,却是扎扎实实稳定受控的挣扎,自然也好人性也罢,握紧择善固执的信念,风雨过后还能再看见花蕊上的晶莹剔透。《流鸦》创作灵感来自梵高画作《麦田上的鸦群》。若乌鸦作为最终解脱的象征,或那些人们欲挣脱的念头,人在这盛满绝望与痛楚的世间就像一头荒野间艰难爬行的困兽,乌鸦落在了逐渐失去支撑力量的兽身上,爪子慢慢陷入肌肤,带走了残存的坚持同时也失去本非源源不绝的养分,在时间推移下一同造化成沙。《荒岭十二象》世界是座巨大的牢笼,当匮乏充斥人间,人性仅是牌坊,人们在看不见的屏障里无意识的表演着,荒诞成为习以为常的剧码,理智则成为不切实际的奢侈品。“凭谁都无法在世间繁杂的剪不断理还乱中独善其身”— 《本恶》、《蝇》、 《击鼓传花》混迹混沌本就难独善其身,沿路总有蝼蚁缠身,独自踽行人间不时时跟心底的自我说说话,怎能确保两个自己在同一条道路上,就像《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中的查理,即便透过手术提升了智识,能解开世间多少学问上的难题,但未跟上的心智仍像个孩子,皮囊因粮食成长,灵魂用自省喂养,在一个个被包装的善意或恶意的冲击下,用诘问与对话灌溉灵魂,每一个回忆都是面镜子,折射着自我的每一段序列,“心里若没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是看不到的。”《本恶》一句无心的喟叹,一句平凡而受世间人普遍认同的话语:“小孩多可爱”,成了一首歌曲诞生的契机。年幼的人类因无穷的潜力与无知亲手铸下了多少生命的消逝,善良是因为觉察到恶意带来的苦痛,在还未品尝到痛楚之前,谁又能懂得良善背后的慈悲。《蝇》“这是一首决心将心中尖锐与反叛一并奉告的产物”,从不愿做趋炎附势之辈,也不愿仅当个探测喜好的风向标,从所看所闻所想中孵出的意识花朵,只盼望它随着本该长成的模样降生,而不是泡在口沫中腐化,“清醒知道自己是谁的重要性胜过存在在别人为你构建的条条框框之中,设限无论对人对己,都是罪行的一种”。《击鼓传花》创作源自周边朋友受谣言所累之经历,亦是对网暴与键盘侠的真情奉告,既非事主亦非关联之人,看客嘴上无心的一两句话,可能是他人心口上的一枪,似逞一时口舌之快就能高人一等,“看人出丑及谈论是非仿佛已经变成了一种诡异的游戏”,但风水总是流转,总有天看客也会沦为局中之人。